1. 古时候日常生活是说文言文吗
文言文是用古代汉语写的文章,流传到现代的古汉语书面材料,以甲骨文为最早,离现在有四千年左右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记载史实和科学成果以及阐发哲学、政治观点的作品大批涌现。《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出的596位著作家所写的13269印卷作品,大多产生在这个年代。
后代的知识分子,从唐、宋直到元、明、清,他们写文章,从用词到语法都以那个时代的作品为规范,这就是文言文。
文言文与古代著作是两个概念。
虽然大部分古代著作包括文、史、哲及自然科学著作都是用文言写的,即沿用先秦时期的词汇与语法写的,但其中一部分古籍也有用当时的口语写的,有人称它们为古白话,如唐、宋的“传奇”,明清的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等。反之,现代人也有用文言写文章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 的一些书信等。
=========================================
换言之:所谓的文言文,即沿用先秦时期的词汇与语法写的文章,而不是所有古代的著作。古人日常说话,当然更不可能用文言文,但是因为时代间隔的关系,他们的白话文放在今天来看,还是有些古文的味道……
2. 古代是说文言文的吗文言文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他们的口语是比较生活话的。
就像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也有区别一样,只是随着汉语的发展,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没有那么大了而已。古汉语的书面语即现在所说的文言文因为和人们的日常口差异太大,普通人(没学问的人)听不懂,所以近代才会提倡白话文啊。
官话、吴语等,其实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和方言,这和文言文是书面语、口语没关系。古汉语的声调的确和现代汉语不同,有五个声调,但是这也只是汉语的语音问题,可以看一下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史》。
3. 中国古时候说文言文,现在说白话(普通话)那新加坡等也是说汉语的中国说文言文的时候是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中国还处在一个封建时期。那时候的航海业还很落后。汉人文化还没有传到那边去的。
我们假定用封建时期定位你说的“古时候”,那时候的“新加坡等”还是原始社会没脱干净,语言应该是用“土话”(估计还要配手语的那种),就是现在有些亚马逊丛林或者中南美无人岛上的原始部落那种形态。
所以他的“古时候”和我们的“古时候”是有时间差的。我们在封建末期,其实“文言文”就已经结束了(估计那时候新加坡还是用土话)。用越南来举例:他们的语言都是在一战和二战后,由法国人给他们编写的,之前他们还是用土话。新加坡有文字和正式语言的时间应该是大量华人迁徙的时代。那最起码也要追溯到比“郑成功”还早的时候。
总之我认为新加坡的语言历史绝对是由“土语”迅速转变为“白话”,中国古语(即:“文言文”)时期,在他们的语言演化历程中过度时期很短,甚至没有。应该是后期我们中国已经讲白话的移民带去的。
另外,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研究不仅仅是“新加坡等”的历史,更应该了解中国的岭南、南粤、闽南等沿海地带的文化发展历史。
4. 古时候的人说的话是文言文还是普通话方言自古有之,古人说的话首先是自己的方言,不同方言间的人使用官话(古代通用语,就像今天普通话作为通用语一样)。方言不断在变,官话也不断在变。文言文作为古人说的话的书面语,虽然比较稳定,但是跟口语相差到一定距离后也会逐渐改变的。
所以,古人说的话,只能说是古代的方言,而在与不同地方的人交流时用古代的普通话!所以是哪的人当然就讲哪的话了!如果是当官的或是有身份的人,很多讲官话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了。不过官话也不只一种,也是分地域的。
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成都话、西安话、扬州话为代表。华北官话、西北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分别通行于中国南方除吴、赣、湘、粤、闽、客家等方言区以外广大地区的西部和东部。 官话内部一致性比较大,除了南方地区的部分官话之外,大部分地区都能够彼此通话。
“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雅音、通语、正音,明清称为官话,清代又开始称为国语,1956年改称普通话;而官话一词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5. 古代人说话说的是文言文吗古人和我们说话完全不一样,古人要是复活我们肯定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现在的南方方言更接近古代口语,保留了一小部分古音方法,所以南方方言很难听懂,比如吴语、粤语。当然古代也有方言之分的。
古代也有官话,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一种共通语,是做官的人便于行政交流必须学习的语言,所以叫官话,一般百姓如果活动范围广也要使用官话,便于交流。当然官话我们也听不懂。
具体到书面语,你所说的文言文是古代统一的书面语,是古代读书人统一使用的书面文字,你说的史官有可能是说民间很多人不会读书写字,有文化的人根据他们口语的意思记录下来。提醒一下,古代史官写史不是民间采集,只是从古籍中选材料,你说的从事民间语言采集的人可能是诗官,就是统治者派往民间收集民间诗歌的官员,《诗经》就是靠这些诗官做成的,他们写下的基本还是民间的本色语言,但不排除做了文学加工的可能。
总之,简单的说,官话写下来就是文言文。古代也有不用官话写的作品,比如《海上花列传》是用吴语写成。
6. 古人说文言文吗是啊是啊。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需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俗语,指的是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它是相对于文言文而说的。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
所以,是先有文言文再有白话文的。不然你以为是谁说的文言文(*^__^*) 嘻嘻……
7. 古代人是不是说文言文古代人们受教育率很低,只有在写文章时才用文言,老百姓不懂文言,说的是方言型白话。 每个时代为了政令通行,在官员中都使用一种通用的口音,一般就是当时京城的口音,称作都话、官话或官腔,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其实现在的普通话使用北京附近的口音,一定程度上就是袭自明清官话。
较早的时候,当时的书面语言和口语是差别不很大,在当时算是白话(放在今天看就是文言)。大约到了明朝前后,白话与现在语言已相差不多,但由于书籍多是古代传下来的,所以写文章时用的语言和口语就有不同,文言和白话开始明显区别。
汉朝口语说文言文吗
文言文只有在现代的时候才被成为文言文,在古代标点都没有,所有在古文之中有一个词语叫做句读。
文言文以古代的诗词歌赋为例,那都是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弄出来,平民百姓哪里会这个,自然在古代之时,文言文仅仅流传在知识阶层和贵族,生活之中更多的还是白话文,顶多加一个之乎者也罢了。
因此就可以知道古人的话很容易理解,第二就是文言文也并不是很难,俗话说抒情言志,文言文都是抒情类的很简单掌握分段之处就可以理解意思了。
在上古先民时期文字还没有,人们的交依靠的是什么,是自己的嘴巴,正如很多的人说这个字但是却不认识,自己也写不起,在诗经之中的我们看到古代人民知识的结晶那页不是很难,更多的就像白话文一样,不过多了一部分的韵律,有了韵律才叫做诗歌。
在古时候读书的人是很少的,书本非常的昂贵,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就买不起书本,不识字只能说,难道还能够说着之乎者矣这个词语了。文言文在上层社会之中流行,更多的一部分是在押韵和填充词律这一方面。
比如说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本来就只是一个混混,大字不认识几个,但是还是写出了一个诗歌。大风起兮云不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已有猛将兮守四方,这是多么简单地对话,在这个里面你看到的都是很普通的词语,语言也是言简意赅,你在里面看到的顶多就是多了几个感叹词,因此文言文根本就不难了。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出自于古诗文之中,这里面表达的一部分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从事这个行业的都是有知识的,肯定不会有白丁的,没有知识的人哪里懂这些高深的东西。
在古代的文言文和现在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基本上差距不大,只要自己看的多了,理解能力上去了就可以看得懂了,我家里面的族谱就是文言文,历经传承了很多年,从我先祖开始一直就有记载,上面都是同样的话,只是在文言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部分的感叹词。
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文言文不在人们的生活之中,那是在文学上面才有的。
听得多了就能懂了,另外不是每个人都说文言文,因此古人的话并不是那么难理解。
1. 古代人说话聊天都是说文言文吗
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2. 古代人说话说的是文言文吗古人和我们说话完全不一样,古人要是复活我们肯定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现在的南方方言更接近古代口语,保留了一小部分古音方法,所以南方方言很难听懂,比如吴语、粤语。当然古代也有方言之分的。
古代也有官话,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一种共通语,是做官的人便于行政交流必须学习的语言,所以叫官话,一般百姓如果活动范围广也要使用官话,便于交流。当然官话我们也听不懂。
具体到书面语,你所说的文言文是古代统一的书面语,是古代读书人统一使用的书面文字,你说的史官有可能是说民间很多人不会读书写字,有文化的人根据他们口语的意思记录下来。提醒一下,古代史官写史不是民间采集,只是从古籍中选材料,你说的从事民间语言采集的人可能是诗官,就是统治者派往民间收集民间诗歌的官员,《诗经》就是靠这些诗官做成的,他们写下的基本还是民间的本色语言,但不排除做了文学加工的可能。
总之,简单的说,官话写下来就是文言文。古代也有不用官话写的作品,比如《海上花列传》是用吴语写成。
3. 古代人说话都说文言文吗、先秦时文言和口语基本一致中古汉语口语研究尚不足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
《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但是由于书面语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儒家著作经典地位的确立,以及汉字对于汉语的巨大影响,文言文和口语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双轨发展时期。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
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3] (大意为:假、炽、怀、摧、詹、戾、艐这些词,都是“至”的意思……是从古语分化出来的不同说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通用了。)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
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2、唐代出现白话文宋代文言彻底脱节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
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
当时的读书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一般口语要说的意思。宋吕本中《轩渠录》记述了这么个故事:族婶陈氏顷寓岩州,诸子宦游未归。
偶族侄大琮过州。陈婶令作代书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你子,以阋阋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出儿胳胝儿也。”
(应为开封地区方言,大意为:要给孩子买把小剪刀,剪去脚上的硬皮和老茧。) 大琮迟疑不能下笔。
婶笑云:“元来这厮儿也不识字!”[4]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文友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
[5]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点评史书时也是一口白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6]宋人的日常对话,就是这么通俗。
3、皇帝也爱说大白话:成吉思汗和朱元璋的圣旨 到了元代,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很多时候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全文如下: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其实“么”这个现当代汉语常用的语气词,早在唐就出现了,来源是“无”。敦煌写本中写作与“无”语音相近的“磨”“摩”,宋代以后写作“麽”“末”,慢慢地演化成“么”。
至于“么”变成现代更常用的“吗”,那是清代的事情了。明清,白话小说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等,不胜枚举。
皇帝批复奏章用大白话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怒而下诏:“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
钦此。” 相比之下,雍正对年羹尧的那一份表白,是不是显得柔肠百折了许多。
4、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这里有个段子:胡适和黄侃打赌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简洁。胡适对学生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
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绞尽脑汁拟定了电报,挑出字数最少的一份,写的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
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二、对古人的误解源于重文言、轻白话 梳理了从先秦到五四,书面语和口语、文言和白话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最早在唐宋时,当时古人的口语就和我们现在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我们总有一种错觉,觉得古人说话都是那么佶屈聱牙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话文出现时间晚,且被传统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虽然使用先秦口语的“十三经”到了后世已经成了难懂的文言,连汉人的批注对唐宋人来说也很古奥。
可是,儒家经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参加科举就不得不学。除了功利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书信,也都必须使用文言文。
语录体的《朱子语类》里,朱。
4. 古代人说话说的是文言文吗当然不是,文人之间会存在用文言交流的现象,但日常生活还是用白话口语的。
文言文是中国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
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和用“书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
“饭否”就是文言文,这里,“饭”名词作动词用,意思为吃饭。
5. 我问一些中国古代人说话都是说文言文吗不是的。在古人的生活中,阅读,是文言文,说话,还是口语与方言。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口语)、“书面语言”(书面语)来表述,是不同的,比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述,却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
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现今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6. 古代人说话聊天都是说文言文吗古人说的是文言文,还记得史记上的记的陈胜说的那句话吗?“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里是引用陈胜做平民时的原话。
越是古老的时候平民说的话越是难懂,《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三国》和《水浒》就是明时的白话文,就跟现在的语言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所说的文言文,是远古时期人们说话,成文当然与口语稍有不同,但差别应该不大。
后来,在文章中沿用下来,而口语变化较大。到唐宋时代,文言与白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
后来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就用了当时的白话。白话文的普遍使用是在近现代。
其实现在还有一此地方方言中残留古人说话的影子,以厦门话为例,“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有没有?”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
7. 古代人是用普通话说文言文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于是一般的人就认为文言与白话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而且从来就是如此。如果从古代的历史文献与少数存留下来的一些白话文学作品相对照,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这一点可以参考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便很清楚。除此而外,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留下来的朱批中就有从白话到文言的的修改。光绪十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批阅奏折。其中有一份朱批原来写着“你们作督抚的”应如何如何,后来又在旁边用小字注着“尔等身膺疆寄……”,这就是从所谓活生生的口语变成文绉绉的文言的典型材料。再看元朝的白话碑,明太祖朱元璋立于孔府的碑石,都是皇帝官府的命令,但都是彻底的白话,与史书所载文言的诏书完全不同,的确证明文言与白话之间差异很大。但如果秦汉上古看来,文言与白话未必就有这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古人说话大多是文绉绉的,不大有所谓文言与白话的不同。
虽然古代的白话材料我们今天已经不易得到,但由于南方方言保留着古代汉语的形态,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方言口语中去窥测古代人说话的样子。以厦门话为例,在日常口头语中就很多是今天所说的文言形态,如中国人最普通的问候语就是“吃了没有?”,厦门话只说“食未?”。问人家“有没有?”厦门话只需说“有无?”如果问得详细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厦门话则说“到底有抑无?”这里的“抑”字的用法,现在只能在文言文里读到,如“抑或”一词,但却正用于今天厦门地地道道的口语里。所以上古文献中我们读来不易的文言其实恐怕都是当时的口语。如果认为上面的实例过于简单,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些稍复杂的例子来。厦门人批评操之过急的人常说,“未曾学行,就要学飞。”亦即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要学着飞。“未曾”二字是典型的文言,但在厦门却是口语。再有十数年前颇为流行的通俗歌曲“酒矸倘卖无?”,差不多所有非闽方言区的人都不知其为何意,但厦门人却很明白这就是“有没有空酒瓶可卖?”的意思。将无字放在句末,又用上“倘”字,是文言的表达方式,但至今却仍用于方言的口语中,可见文言与白话在古代相去的确不远。当然,厦门人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说的话其实就是古代的文言,因为现在“抑”寥纭鞍?保?拔丛?钡摹霸?倍寥簦?ing〕,就连说话者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这些字眼了。其他方言也有类似现象,不遑多举。
五四运动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至为激烈,先知先觉们多认为文言是统治者创造出来愚弄老百姓的东西,甚而认为汉字的难学难认也是治人者有意为之,因而有人至于主张将汉字丢到毛厕里头去。其实平心看来,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以及汉字的繁难复杂本来是语言文字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要形容的事物越来越多,要表达的感情越来越丰富,语言文字也就发生了从简到繁的变化。上古时代多是单音节词,亦即一字一词,为了表示更多的内涵,一是增加汉字,二是出现双音节词乃至多单节词;在口头语言方面也是如此,越简单的话越容易含混,于是用词时就不但增加了音节,而且改变了表达的方法。这些改变不但是汉语本身发展的缘故,还与外来影响有关,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佛教文化的东来,双音节显然增多。北方草原民族的不断南下,也肯定要对口语的表达方式有所影响。人随时随地要说话,但不是时时刻刻都要写文章的,显然口头语言的变化很快,书面语言的变化就比较慢,因此逐渐地,文言与白话的距离就越来越大,以至于到后来,文言白话明显为两途。
其实文言本身非无变化,我们只要看看《尚书》里头那些诘屈聱牙的篇什与清末的新民体文章的差距,就可以了然了,但这种变化与白话的变迁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文言与白话距离逐渐加大以后,识字者与文盲之间,上层社会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既能说白话又能识文言者,自然比只能讲白话而写不来文言的人要高一等了,于是人为的差别又更加大了方言与白话的距离。白话文并非从五四运动起才有,晚清已经有不少人将口语写成了文章,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使文言文在二三十年间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白话文的一统天下,现在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异几乎已经不存,但会写典雅文字的人也没有了。据说修清史的事将要提上议事日程,不知是用文言撰述呢,还是用语体文来写?
8. 古人是怎么说话的古代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比如春秋战国是古代,宋朝,明朝对我们来说也是古代。但是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对于宋朝、明朝来说也是古代。
先秦时代的口语其实就是后来的文言文。《诗经》里的风就是民风,就是当时最通俗的流行音乐,但是正是这个“风”对我们来说并不通俗,甚至对唐宋人来说,也不算通俗。因为先秦的方言和通俗语言在后来的演变中成为了文言文,也就是所谓的古文。
在唐朝中期刘宗元和韩愈推行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提倡恢复先秦的语言系统,将先秦的白话作为行文的语言。
而在唐朝,白话早已经和文言大不相同。到了宋元明清,民间的白话文化更是与现在的白话差不了多少了。你可以看看元朝的套曲(南曲和北曲),这种戏曲的剧本其实都是用民间白话写的,非常口语化,你也可以看看宋朝时候朱熹的文章,虽然宋朝理学是中国哲学中最晦涩的部分之一,但是朱熹的文章却非常地通俗;明清时候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白话文小说,其中又以《水浒传》的语言更接近白话,因此《水浒传》和《金瓶梅》成为通过语言了解明清市井生活的很好的资料。
《红楼梦》是白话小说的最高峰,《聊斋志异》则是文言文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死的那年正好是曹雪芹生的那年,两书几乎在同一个历史时代,这正说明了白话文和文言文是同时存在于中古人的语言系统中的。
直到五四运动、新文学运动之后,胡适提出《文字改良刍议》,并且亲自尝试了第一本白话诗歌集《尝试集》,鼓吹用白话文,这个时候白话文的地位如日中天,加上近代化、现代化的步伐而最终几乎消灭了文言文的存在。但是白话文并不是胡适发明的,在此前的一千年前就早已经出现了。
本文来自作者[雨樊]投稿,不代表机氪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jpker.com/jke/5268.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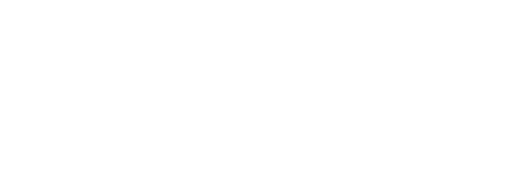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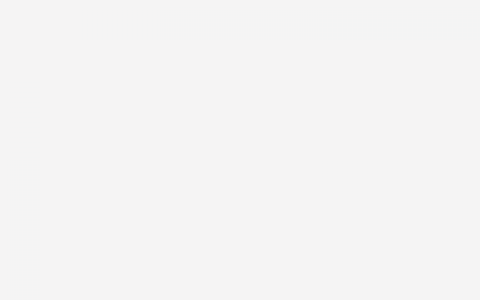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机氪号的签约作者“雨樊”!
希望本篇文章《古时候是说文言文吗》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机氪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1. 古时候日常生活是说文言文吗 文言文是用古代汉语写的文章,流传到现代的古汉语书面材料,以甲骨文为最早,离现在有四千年左右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记载史实...